附录I 她们如何以二的方式工作
亲爱的德尔赞特[1]:
您问宇佐见莲子与我如何相识,如何一起工作。我只能给您看看我的观点,莲子的说法应该是不同的。当然,我们知道,两人同行没有秘诀或者一般的程序。
 (资料图)
(资料图)
那是我到日本的第二年,天底下又一个六八年。起初我们并不相知,后来您知道的一位老师要她来我们学院帮些电工、印务和档案的活计,那时我也早就借从前在古文书预科班的便利,在档案室帮工。最开始,我们都没什么可供对方互相了解的。能看出她已经有了走时精准的行动时钟,在物理学家和工程师之间辗转,参与那些个计算组、实验组和里里外外的学生自治组织的事务。她那时已经是个像海的人,她的表面千变万化,像浪尖折光的波阵面(这个喻体是她告诉我的),而不是单一颗星。她为各方通风报信,在京都不算大的地域里四处游弋,不停下,不中止。她具有惊人的速度,正是她的物理学会告诉我的那种。至于我,我更像山丘:我很少移动,不能同时用法语和日语两种语言记笔记,思想有了运动也不会叫人看见。我一个人写作,不爱用任何一种语言说话,不声称自己能注意到人不能见的视差。我们俩的起点因而是棋逢对手,相扑比赛。
您再打量一下,她在两个活动之间、在人群里面的样子。她的确陷入巨大的孤独里面,她溜走了,去阅读,写作,找窗架望远镜。所以混乱结束,您那老师把她要回去之后,她还是爱上我的档案室来。我很少遇上她那样的人。她不断给出理念,对它们反复考虑,一再调整,也可以轻易地丢掉、忘记它们。她的大脑是块黑板,她脑中所想,跟她在黑板上留下的粉笔字迹图示的变幻运动,协调同一。所以她有一种非常神奇的信念——日光之下仅有真事。我误解她的这个信念很久,错从客观性的理解出发,把她仅当成有幽默感的实在论者许久。直到有晚我给她念我的人类学笔记,告诉她,日本人的神明妖怪,先人定位为人的记述、技术和自然的踪迹种种之间历史地建构出来的杂合体;但是,按相对性精神学,也按充足理由律的意思,这些在观念里的踪迹有着现实的来源,Ghost in Shell的Shell(与常识相反)。而她,用附近洗手间里的长水池,报我以一份物理学谓孤子的妖怪二百余年来的生活史的速写:一个在我们二人眼中无可置疑地真实的波峰从水池的一侧跑到另一侧,来回反射,直到深夜熄灯都没有停下,像是灵摆的摆锤或者理想的陀螺。我不想,或不敢问她,这个水波是否应该衰减停下;她也对我声称妖怪如实存在没做质疑。我们不是同在梦中,就是有默契地携手跨进了所谓二联性精神障碍的境界,正如其法语原名Folie en Deux所说。
在两类私人的谵妄之间,我们想要一起工作。凭着在戴安全帽的青年斗士中间学来的政工技术,我们要了点经费和一间活动室,成立了秘封俱乐部。就名义上而言,我们调查虚实不能决定的事物,当然我们也不知道如何着手。我们搞来许多报告,一起阅读比对,在一周后的凌晨2时17分翻墙进入莲台野去复原一张念写的拍摄现场。或许是有什么东西希望再次梦见我们,在巴比伦的彩票上下了高注。我们四处搬弄卒塔婆,在推定的丑正三刻转动照片里的墓石,石骰落地般的一声,我们如实如期望地到了那张念写拍到的寺院。
她对我能看见无人能见的间隙有所敬畏,我也害怕她能够把目力所及在那本大书里面索引罗列的眼睛。但很快,我们便对接纳了对方之后愈发狂放的现实(您知道,我只在十来岁时能确认自己醒来与否)有所构想。我们的工作中充满混乱无序的SNS通讯和手稿交换,两个人几周或者几日见一次面,尝试发现中古店、在鸟不拉屎的破神社盗拓碑文,或者站在京大的老水池边上,用演示射影变换的几何玩具偷渡到月球去。为了收拢这些调查资料,我们开许多玩笑,阐发不同方向的意见,混合语言和用词。我们的簿记工具从笔记本演化成了空白的速记卡,因为后者易于打乱顺序,当作透特塔罗的扩展使用。
卡片不需要署名,但我们之间没有完全地协调。我们互相责备某张手稿上的某行或者某个图示没有被接通,见面的时候也很少同时开腔,总是一人说,一人听,眼神竞速追赶。我能看到相扑场的那个圈围在我们边上,因为我们不在任何事情上完全一致,我们的经历,我们留下的踪迹,我们周身的东西都独立地持存。每次我们加以重提,它们都提出我们未曾有的见解。
从鸟船遗迹回来之后,我的视力有大的增幅,也能在各个相近的世界之间更加轻易地往返,带一些所谓的欧帕兹回活动室。我也出了进研究生院以来的第二本专著,关于“后马拉美主义”诗人的。而她,或许是在街上吃的催泪弹太多,或许是因为她不搞弦论一系的物理,转去搞谱几何相关的学问的缘故,她的有限的视力开始衰退,无限的部分则跟她日渐敏锐的听觉联盟。她能听出鼓的形状(并跟我强调,数学地说,不是总能做到——形状不一的鼓可以有一样的声音,能看出来),不再区分所见和所闻,全部信以为真。
的确,我畏惧她的力量,正像她出于视觉上的无力畏惧我。并且,我们互相都能猜到对方想要说什么,也知道对方猜得到自己会如何回应,我们也已假设有更加复杂的东西激动着周遭的世界。爱人之间的忠诚测试并不是我们需要的。为了把我们之间的新境界良好地考虑在内,为它摹像,我们决定诉诸狂人之间的方法,做一本书。
我们两人的合著不是两人共谋的尝试。我们有成堆的速记卡、照片和草稿纸,活动室里有一大块线索墙。我们用这些与我们各自共谋的棋子进行了漫长艰难的棋局,中场休息是在京都愈发复杂的老城区后巷之间愈发难以理解的迷失,我在稍微接近梦境的时间段里也常常看见物理学家只敢去假设的、极端微小或转瞬即逝的东西。我们用互相的辩论替代战棋中常见的掷骰,再用大段的省略为其加速(莲子的说法:有限时间内加速到无限快的解会破坏牛顿因果性)。这样的争夺延续了百科全书派以来的传统,我们准备一个神秘的笔名,写下非常多的句段、设计非常多的地名和角色,我们在这棋局的最后汇编出一本博物志,它的创作过程、它的词典、它的作者(们?)的冒险、它的草稿图示和一张做了分形处理的京都市地图作为一些蛛丝马迹形成的网格参与其中。如果您把这本书谈论的奇异,和它后来引发的一些小而奇异的事件考虑在内,回到我当年跟莲子的说法,这本叫《燕石博物志》的书,是一只器官完善、活动正常的妖怪。
您和很多人读了这本书、看见了这本书,但没有人能证明他看见过这只妖怪。这不稀奇。没有人能够证明“巫女、巫婆、灵能人士、超能力者、经济学家”(《燕石博物志》日文版,第三章A1节)看见了他们才能看见的东西。再换一个例子:锆石晶体,和它上面能看出来的、没有人胆敢不以假设的态度讨论的前生物的整个的地球。
考虑到它们通过不安和焦虑的踪迹得到定位,可以确信妖怪生在人心的罅隙之间。神妙的东西也居于视与听,还有更多的感官之间。地球的存在,地球的历史,物质的精微和时空的微小结构,所有这些东西都以近乎妖怪的样态存在着。所有这些东西都存在于境界线的后面,都在某种视差的射程内。宇宙的这种无尽外推的渗流结构真实得叫人焦虑而难以忍受。我们都接受了对方那恶心得难以忍受的眼睛作为宇宙之窗的事实。我们的二人同行也从未离开这个视差投下的境界线。
好了,德尔赞特先生,我希望能回答您的一部分问题,祝您的翻译工作顺利!
中译者注
[1]: , 系宇佐见莲子和玛艾露贝莉·赫恩的法译者,两人校友。本文最早见于法文版《燕石博物志》的译后记,标题也为法译者补充。
标签:

03-18 14:53:54

03-18 14:51:07

03-18 14:47: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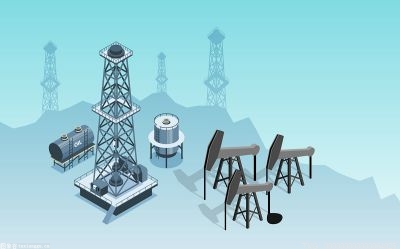
03-18 14:44:44

03-18 14:40:44

12-04 14:30:57

